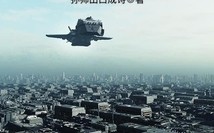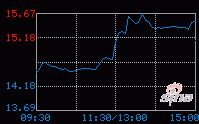马尚龙:上海欢言谁与共
百来年前,因为创造了诸多 “远东第一”的纪录,上海便有了“大上海”的美誉。
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,“大上海”是上海的骨骼、相貌、血型、性格……还应该有一个“小上海”,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,是弄堂里的上海,角角落落的上海,锱铢必较的上海。小上海不是棚户区、下只角和收入低、学历低的人群,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。

大上海和小上海,看似对立,实际上,大小上海的叠加,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。只不过很多时候,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,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,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,对小上海之“小”,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、之通达上海周身,还是轻描淡写居多。
引发我这番思考的,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“同途殊归”——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,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,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,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。
笃笃笃,卖糖粥,三斤胡桃四斤壳,吃侬肉,还侬壳,张家老伯伯,问侬讨只小花狗……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。童趣,美好,幻象……谁都无法解释,糖粥、胡桃、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。不要紧,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。
童谣没有时代指向,没有贫富贵贱,无痛无疾,满足了童年的美好。
在童谣之外,还有一种哼唱,也朗朗上口,但是和童谣之间,看似完全不同的“三观”。
“1958年,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”“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”“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”……
一点不美好,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,塞满了日子的窘迫,生活的尴尬,体面的缺损。还很刻薄,让人备受讥讽、歧视和起哄。不管是在什么年代,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。
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,顺着弄堂,顺着学校操场,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,蔓延、传扬。
我把它们称为“俗语”。不雅,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,直达市井的笑点——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。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,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。
俗语,自有它不俗的内核。
俗语有稚趣,有野趣,有智趣,还有年代之趣。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,也是成人的语境,不像童谣,只是稚童的幻象。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。
俗语是杀器,重在精神杀伤;伤害不大,侮辱很大。但是这种杀伤,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,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。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,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,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。比如用“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”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,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,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。
俗语很俗,却俗得有底蕴,每一句俗语,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,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。比如,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,至今还被叫作“小喇叭”,谁能想象得到,“小喇叭”的梗,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《小喇叭》?
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。想一想,“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”,为什么弹的是琵琶,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?我简直怀疑,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,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,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,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口拈来。
越是贫穷窘迫,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无限。如今,日子渐渐安逸,俗事少了,俗语也没有了。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想起了某一句,这时候的俗语,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,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,打开来,漂流瓶里装着的,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,一幅“珍宝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。
俗语就有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意义,是回望上海贫穷苍白年代的一个小孔。
俗语的嘲是真的,笑也是真的,幽默在刻薄中滋生。市井之笑语,市井之欢趣,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,甚至可以这么说,那个年代的欢趣值,高得不可思议。
上海俗语,就是上海欢言。加了书名号,《上海欢言》是我的新书书名。
欢言谁与共?你我世俗人。
李白有诗句写道:“欢言得所憩,美酒聊共挥。”大意是说,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,畅饮美酒,宾主频频举杯。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:“欢言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。”诗意更加直白,无须解释。以两位大诗人的“欢言”诗句,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,倒是别有意思的。
欢言是生活状态,且有生活情景。从中也可以推断出:有欢言的生活,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。
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,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。弄堂、石库门的俗常欢趣,是欢言的母体。人人都有故事,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、无处隐身的舞台上,只在于舞台的追光灯是在追谁。有含辛茹苦的正剧,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,有鸡飞狗跳的闹剧;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;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,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……
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“欢言”诗句之高低,但是完成《上海欢言》书稿时的心境,更贴合的似是陶诗——“欢言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。”(马尚龙,本文节选自作者《上海欢言》自序)
南妮:喜剧的上海就在侬身边——读马尚龙新著《上海欢言》

“从1958年开始走向社会的85万妇女,热火朝天一阵子后,有一些重新回归家庭,她们既承受不了每天上下班的节奏,更看不下去自己孩子的邋里邋遢。”这篇《“紫丁香”绽放在1958年》的文章中提到的“紫丁香”,是紫药水点在孩子生癞痢的脑袋上,“用毕加索的夸张变形手法来描绘,那就是头顶上的紫丁香了。”套用马尚龙另一本书的书名《为什么是上海?》问:为什么是1958年?浮夸年代的热浪,被炎夏弄苦的爹娘,群体性出生的小癞痢……1958年,喜剧的精神就已经在上海的弄堂里奔腾。原来上海人一直有把历史的局限演绎成戏剧,把人生的困境拿来一笑的本事。《上海欢言》是上海可爱的故事书,也是上海珍贵的民俗学,喜剧的上海,是马尚龙的描摹,也是马尚龙的创见。
物资匮乏年代的流行语,如果与“食”有关,那是太正常了。“我不是吃素的。”“隔夜饭也要呕出来了。”“人参吃饱了。”“污搞百叶结。”“吃过洋面包。”“奶油包头,奶油小生。”——遥想图景,会心而笑,那些“食言”之下的“欢言”,它们透出多少时代文化的特征与城市习俗的犀利。作家妙笔勾勒的,是漫画般的叠影。上海,不大见迂腐的书生与狂飙的诗人,即使是历史性物资的匮乏,即使匮乏的是民以食为天的食,上海人还是在笃悠悠地自嘲,也以自嘲的勇气在嘲人。于是,大街小巷流行的俗语闪现着可观可喜的娱乐气氛。马尚龙认为,上海人有着自嘲精神,所以不怕嘲笑他人。“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。”喜剧精神来自于骨子里的刚强。
《亭子间春光秋色》一辑,“亭子间”上海文化的解读流光溢彩。马尚龙说:“逼仄的空间,挤迫式的天地,粗陋的表情,嘈杂与骚动……恰恰是缔造了最有画面感最有戏剧冲突的舞台。”外在需要文明,内在保护隐私。“石库门天生就是一个表演喜剧的舞台。所有石库门题材的影视剧,通常是轻喜剧风格。”要对生活有着怎样的热爱,要对自己有着怎样的信心,这个城市的人才能勇于表现:所有的窘迫里都有欢乐。笑是智慧,是力量,是创造,也是生命的诗意。《弄堂喜酒弄堂婚》,因为穷,因为“饭店重新开放喜宴是在1973年”。弄堂婚礼的酒水,摆在隔壁邻居家里。石库门喜酒最大的亮点是:新郎新娘“近亲结婚”概率很高。可能新郎家住弄堂的这一头,新娘家住弄堂的另一头。但是租的婚车出租车,是“要到热闹的地方兜一圈,又回到弄堂口,新郎新娘走进弄堂,算是乘过婚车了。”马氏冷噱,有着感人诗意。《夜饭连着夜报》里,一家之主的父亲,从下班回家到吃饭,吃好晚饭,“在老位置上坐下来,一张夜报,一杯茶,一支烟。”长幼有序,饭桌规矩,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。“螺蛳壳里做道场。”——尊、理、乐、美。它们都是上海人的道场。
以《现代汉语》一书闻名的汉语语法学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胡裕树教授是马尚龙的偶像。《上海欢言》与马尚龙系列上海题材的散文集一样,体现着他冷隽风趣、幽默恣肆的语言风格。修辞仿佛是终极目的,修辞本身产生灵感。上海应该是马尚龙最忠诚的修辞课。分寸、路数、市井,他的书是最文学的上海学,是最上海的风俗论。
马尚龙的《“沪版”老实人》一文曾经被无数读者点赞。他认为“上海是老实人的盛产之地。因为在老实人头顶之上,有老领导,有老法师,他们是上海公序良俗的隐形护卫者。老实人则是与他们组成三者合一的方阵。”“上海的老实人,是信任社会承诺的人;是服从社会安排的人;是接受环境生存的人;是律己高于律人的人;是追求人生格局的人;是习惯于有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人;是将诚信定格为血型、将体谅当作责任的人。”
上海的老实人正是上海喜剧精神的缔造者。无论歌咏还是反讽,上海人心中的神诗意而遥远,他们通常以否定来表达肯定,以满不在乎表达深情。老实人免不了有些腼腆。腼腆可以是戏眼,琐细能滋生笑意。博士毕业的新上海人,千万不能低看上海街头的老克勒无名大叔。从沧桑的岁月中走来,上海人抓住生活的每一点材料自娱也娱人,他们永不沉沦。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·朗格说:“正像说话是一种精神活动的顶点一样,笑是感情活动的顶点——感觉到的生命力浪潮的顶点。一种突然的优越感,需要这样一种生命情感的‘升腾’。”上海有欢言,上海才发展。喜剧的上海,马尚龙虽然没有为上海作新的冠名,但是《上海欢言》真正将我们鼓舞了。“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。”(《上海欢言》自序)那么,上海人的笑,应该是蒙娜丽莎永恒之笑。(南妮)
相关问答
欢言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是什么意思_作业帮
[最佳回答]快地饮酌春酒,采摘园中的蔬菜】读山海经(其一)(东晋)陶渊明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.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.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.穷巷隔深...(...
酒好备客难请诗词?
1、唐代:李白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原文选段:欢言得所憩,美酒聊共挥。长歌吟松风,曲尽河星稀。释义: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,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...
酒杯欢言打一动物?
鸡(喝酒水后剩酉,酉属鸡。酒杯欢言缺了美味的鸡又何来言欢呢?)鸡(喝酒水后剩酉,酉属鸡。酒杯欢言缺了美味的鸡又何来言欢呢?)